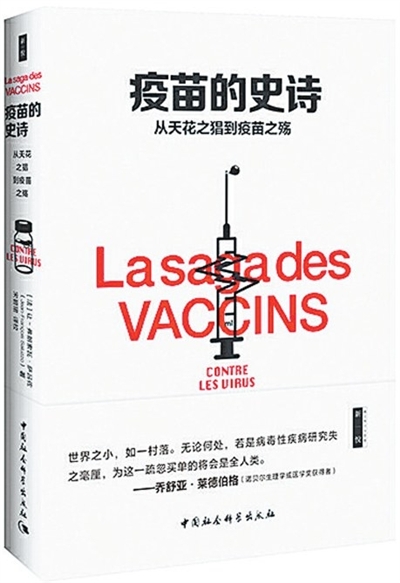相關新聞
-
我市累計接種新冠疫苗超100萬劑次
記者了解到,市民接種疫苗的主動性很高,不少已經接種過疫苗的業主表示,接種疫苗之后感覺很安全、很安心,為自身健康提供安...
-
疾控專家解答新冠疫苗接種相關疑問
對于接種新冠病毒疫苗,市民還有不少疑問。針對這些問題, 5月23日,省疾控中心傳防所計免部部長王雷進行了解答。記者:針對...
-
湖北不斷優化服務滿足疫苗接種需求
湖北日報全媒記者胡蔓龍華曾莉通訊員張春紅郭霏5月23日,全省新冠病毒疫苗接種超過3000萬劑次,全人群接種率穩步提高。據介紹...
-
中國國藥新冠疫苗獲世衛組織緊急使用認證

世界衛生組織7日宣布,由中國醫藥集團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研發的新冠滅活疫苗正式通過世衛組織緊急使用認證。它也是第一款攜帶...
-
湖北省新冠疫苗接種突破2000萬劑次
5月6日上午10時40分,極目新聞從湖北省衛生健康委員會獲悉,截至5月5日,全省累計報告接種新冠病毒疫苗2016.5324萬劑次,最大...
-
單支兩人份包裝新冠疫苗將上市 省疾控中心:接種效果不受影響

5月7日, ,本周我省會有部分接種門診收到兩人份包裝劑型新冠病毒疫苗,前往接種疫苗的居民可能會發現接種人員取出1支新冠疫苗...
-
三針疫苗vs兩針疫苗!專家解答
首批“重組新型冠狀病毒疫苗(CHO細胞)”現已在湖北投入使用成為滅活疫苗后又一款開放接種的疫苗這款疫苗的安全性如何?答:...
-
探訪武漢“重組新冠病毒疫苗”注射,三針劑要這樣打

極目新聞記者陳凌燕? ?通訊員劉翔首批重組新冠病毒疫苗(CHO細胞)已經在武漢投入使用, 4月20日,極目新聞記者來到漢陽區...
-
重組新冠疫苗安全性可以保證
近日,首批“重組新型冠狀病毒疫苗(CHO細胞)”在湖北投入使用,成為滅活疫苗后又一款開放接種的疫苗。答:目前使用的重組新...
-
新冠疫苗不打第二針會怎樣?有最佳間隔時間嗎?最新回應
從前期新冠疫苗臨床試驗研究結果和使用時收集到的信息,新冠疫苗常見不良反應的發生情況與已廣泛應用的其他疫苗基本類似。去...
① 凡本網注明"來源:咸寧網"的所有作品,版權均屬于咸寧網,未經本網授權不得轉載、摘編或利用其它方式使用上述作品。已經本網授權使用作品的,應在授權范圍內使用,并注明"來源:咸寧網"。違反上述聲明者,本網將追究其相關法律責任。
② 凡本網注明"來源:xxx(非咸寧網)"的作品,均轉載自其它媒體,轉載目的在于傳遞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網贊同其觀點和對其真實性負責。
③ 如因作品內容、版權和其它問題需要同本網聯系的,請在30日內進行。

娛樂新聞
-
人藝“經典保留劇目恢復計劃”開篇之作 《風雪夜歸人》4月25...
 2025-03-27
2025-03-27
-
摘下神探濾鏡 《黃雀》講述充滿“鍋氣”的人物和故事
 2025-03-27
2025-03-27